作者简介:
郑飞,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导、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
2024年以“智驾元年”之名载入史册,开启了我国的智驾“狂飙”之路,形成了华为、自研、Momenta智驾方案三足鼎立之势。据统计,中国乘用车L2级新车渗透率已近60%,并有望于今年突破70%。随着自动驾驶技术的普及,L2级辅助驾驶功能俨然成为新车上市的标配。
尽管智驾技术给人们出行带来了诸多便利,但其背后也隐藏着不容忽视的法律风险。驾驶员责任模糊、车企宣传失范、系统故障频发等问题日益凸显,亟需通过法律规制与技术协同构建我国智驾安全防线。
一、热问题还需冷思考:从技术崇拜到理性回归
据媒体报道,2024年11月,小米SU7自动泊车事故集中爆发,单日70余起剐蹭事件引发舆论哗然。尽管小米以免费维修和代步补贴平息争议,但事件暴露出辅助驾驶技术成熟度不足与用户盲目信任之间的鸿沟。“SU7高速碰撞爆燃”事件更是为全民智驾热服下“退热药”。2025年上海车展更显“去智驾”倾向,车企的宣传策略从注重智驾技术转向车辆的安全性与可靠性,更加务实。这种降温折射出行业从“技术崇拜”向“安全理性”的集体转向。公众逐渐意识到,辅助驾驶的便捷性应建立在法律与伦理的安全规制基础之上。
技术“狂飙”下,智驾的技术迭代速度远超法律规制的步伐。当前,L2级辅助驾驶仍属“人机共驾”阶段,但法律对“人机责任”的划分尚未明晰,导致事故归责陷入“驾驶员过错”与“系统缺陷”的拉锯战。例如,“SU7高速碰撞爆燃”事件中,主流观点虽然认为驾驶员应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责任,但舆论对车企是否应承担相应产品责任的争议持续发酵。技术狂飙与制度滞后的矛盾,本质是创新效率与安全价值的博弈,亟需法律为技术划定运行边界。
二、全民智驾背景下暗藏的三重法律风险
在智能驾驶已被广泛应用,几乎成为新车标配的背景下,有必要审视其中暗藏的法律风险。
首先,是驾驶员责任风险。不少智驾爱好者认为,启用智驾功能后,系统即全面掌控车辆,自身无需再保持驾驶警觉。此种认识存在严重误区,依照《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的规定,仅当驾驶自动化级别达到L3以上时,系统才对主要驾驶行为(对目标、事件的探测与响应)负责,才有控制权发生“人机转移”的空间。因此,L2级辅助驾驶中,车辆控制权始终、应然由驾驶员掌握。在辅助驾驶模式下,驾驶员始终是驾驶活动的第一安全责任人。从现行自动驾驶汽车相关法律规定看,仅达到L3级以上驾驶自动化的车辆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自动驾驶汽车。如深圳、北京、武汉及香港等地的相关条例均只将L3级以上自动驾驶汽车作为规制对象。因此,辅助驾驶下,驾驶员仍需恪守《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各项规定。
据此,若驾驶员在启用辅助驾驶功能后“脱手脱眼”、分心或酒驾导致事故,可能触犯危险驾驶或交通肇事罪,须负相应的民事赔偿与刑事责任。如,在(2024)苏02民终6213号案中,一审法院认为“自动领航系统仅是驾驶辅助功能,不能代替驾驶员驾驶车辆时的安全注意义务”,二审法院认为“驾驶辅助功能,可以辅助驾驶员,但不能代替驾驶员进行驾驶,驾驶员⋯⋯负有全部责任。”又如,2023年湖北李某、2024年浙江孙某先后因酒后使用辅助驾驶,导致事故发生,被判危险驾驶罪。
其次,是车企责任风险。部分车企为了吸引消费者,在宣传中使用“解放双手”“自动驾驶”“XX公里0接管”等具有误导性的宣传语,使消费者误把辅助驾驶当自动驾驶。这种宣传行为严重误导了消费者对车辆功能的认知,使其过度信赖、依赖辅助驾驶系统,增加交通事故风险。同时,该宣传行为还违反了《广告法》的有关规定,情节严重的,甚至可能触犯刑法中的虚假广告罪。如,有交警部门表示,诸多“自动驾驶事故”均因驾驶人盲信“辅助驾驶”所致。为此,有的车企将说明书变成了免责协议,如,在用户手册中写道“领航辅助无法响应静态障碍物,如前方存在事故或施工区域,请立即接管车辆”。然而,这些躺在用户手册上的“沉睡”条款,并不能证明车企已尽告知义务。
除夸大宣传、混淆营销外,系统漏洞与产品责任也是车企所面临的主要法律风险。辅助驾驶系统存在算法缺陷或传感器失效(如误判施工围栏、未识别障碍物),若事故因技术缺陷引发,车企需承担产品责任。如,2025年2月,湖北一辆理想L9汽车因“幽灵刹车”,引发追尾事故。该案由理想车主承担事故主要责任,理想汽车承担产品赔偿责任。
最后,是法律滞后性风险。针对自动驾驶,现行《道路交通安全法》存在明显的滞后性,法律供给不足,未对“人机共驾”场景下的责任分配作出明确规定。在实际发生的交通事故中,很难准确界定驾驶员、车企以及系统供应商各自应承担的责任比例。例如,当车辆在辅助驾驶模式下发生碰撞,是因为驾驶员未能及时接管,还是由于系统本身的故障,抑或是两者共同作用导致事故,缺乏细化的法律标准来进行责任划分。
此外,现行法律规范未对“接管”的适用情形与前后责任予以明确。实践中,辅助驾驶模式下虽然也存在接管,但该接管仅为技术层面接管,而非法律层面接管,不产生车辆实际控制权及相关法律效果的转移。上述规范的阙如不仅给事故处理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也使得各方的责任难以得到公平、合理的认定和承担,容易引发纠纷和矛盾。
现行《广告法》也未对自动驾驶的宣传标准予以明确。目前,对于L2、L3级自动驾驶功能的定义较为混乱,不同车企的宣传口径和实际功能差异较大,市场整体鱼龙混杂。一些车企为了提升市场竞争力,将原本属于L2级的部分功能,如“车道居中”,包装成全场景自动驾驶进行宣传,导致消费者对车辆的自动驾驶能力产生错误认知。这种技术标准的缺失不仅扰乱了市场秩序,也给消费者的选择带来了困扰,增加了使用过程中的安全风险,不利于自动驾驶技术健康、有序发展。
三、应对智能驾驶法律风险的对策
基于上述法律风险,未来应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规范车企宣传伦理,以司法实践案例不断推动公众认知提升。
在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方面,应及时修订现行法规,以《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为契机,在其中增设自动驾驶专章,将问题频发、舆论热议的辅助驾驶事故责任纳入其中,细化不同驾驶自动化等级下的事故责任认定标准,区分分心驾驶、系统故障、第三方过错等不同情形下的责任承担比例,为事故处理提供法律依据,避免因法律规定不明导致的推诿扯皮。同时,加速推进专项立法。鉴于我国正处于自动驾驶技术大规模应用前夜,技术加速迭代,市场失范显现,传统的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已难以招架。为此,应采取近期修改《道路交通安全法》,中期制定专门条例,远期开展专门立法的形式,加快推动《自动驾驶法》纳入国家立法规划。通过专门立法,明确不同驾驶自动化等级下,驾驶员的法律地位和权利义务,为L3级以上自动驾驶事故的责任归属提供解决依据,补齐法律空白,确保自动驾驶汽车在规范、合法的“高速路”上跑出“加速度”。
在车企宣传伦理的规范方面,应明确车企的风险提示义务,强制要求车企在宣传营销活动中严格履行风险提示要求,采用明示告知的方式,清晰准确地告知车辆驾驶自动化等级。严禁使用“L2+”“L2.99”等字样。车企应明确告知辅助驾驶功能的适用场景和限制条件,向消费者明示辅助驾驶不同于自动驾驶,驾驶员不得“脱眼脱手”、分心驾驶。此外,还需将夸大宣传、混淆宣传等行为纳入《广告法》规制之中,规范自动驾驶汽车广告用语,严禁使用“自动驾驶”“完全自动”等容易引起消费者误解的误导性术语,引导消费者正确认识辅助驾驶的实际功能,避免因误解而产生不安全的驾驶行为。同时,加强行业自律,建立信用公示与行业禁入机制。将存在虚假宣传等违规行为的车企纳入黑名单中,并向社会公示。对情节严重,引发恶劣后果的车企,限制其开展L3级以上道路测试、示范应用活动,促使车企自觉遵守宣传规范,加强行业自律,维护市场秩序,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最后,应推动安全教育常态化,交通管理部门应联合相关社会组织,积极开展辅助驾驶安全科普活动,并将其纳入常态化工作。通过各种媒体渠道,如电视、网络、社区宣传等,广泛传播辅助驾驶的安全知识和正确使用方法,公布典型案例,深入剖析“人机共驾”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风险和隐患。以案释法,通过真实的案例警示广大驾驶员,增强其安全意识和风险防范能力,使其在使用辅助驾驶功能时能够保持警惕,遵守交通规则,确保行车安全。此外,最高人民法院等司法机关应及时发布有关自动驾驶事故的司法解释或指导性案例,明确“驾驶员过错”与“技术缺陷”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和具体标准。如,有针对性地发布若干辅助驾驶交通事故案例,明确“分心驾驶”下的刑事责任以及危险驾驶罪的适用情形,增加刑罚震慑。同时,通过发布司法解释或指导性案例,统一司法裁判尺度,为自动驾驶事故案件处理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和指导,提高司法公信力。
辅助驾驶技术的法律风险本质是技术迭代与制度滞后的冲突。唯有通过立法完善、伦理规范与公众教育的三维联动,方能实现“安全”与“创新”的平衡。未来,随着自动驾驶技术的成熟,法律需进一步探索“系统责任”与保险机制的创新,为人机协同驾驶时代奠定法治基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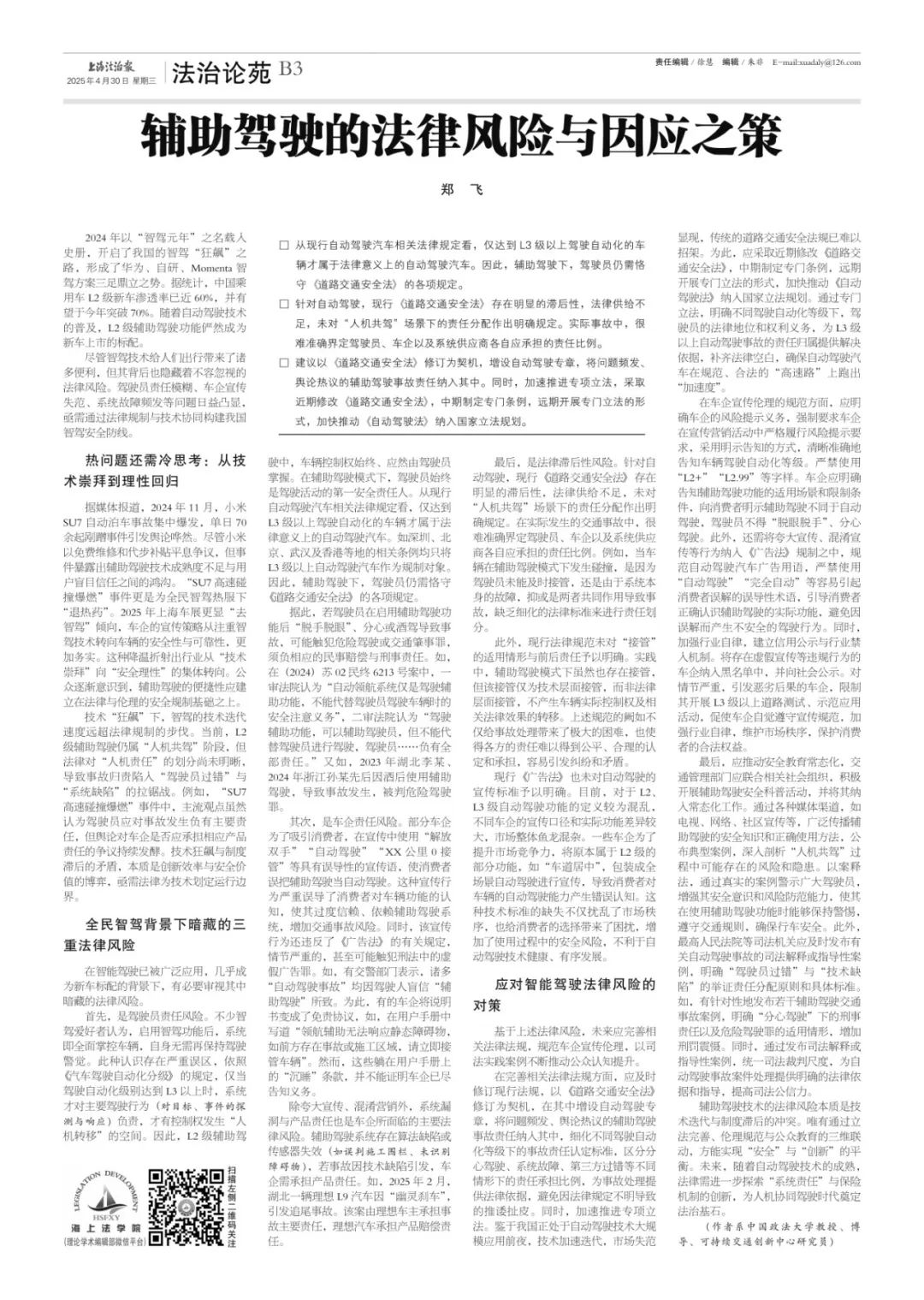
(原文刊登于《上海法治报》2025年4月30日B3版“法治论苑”)

